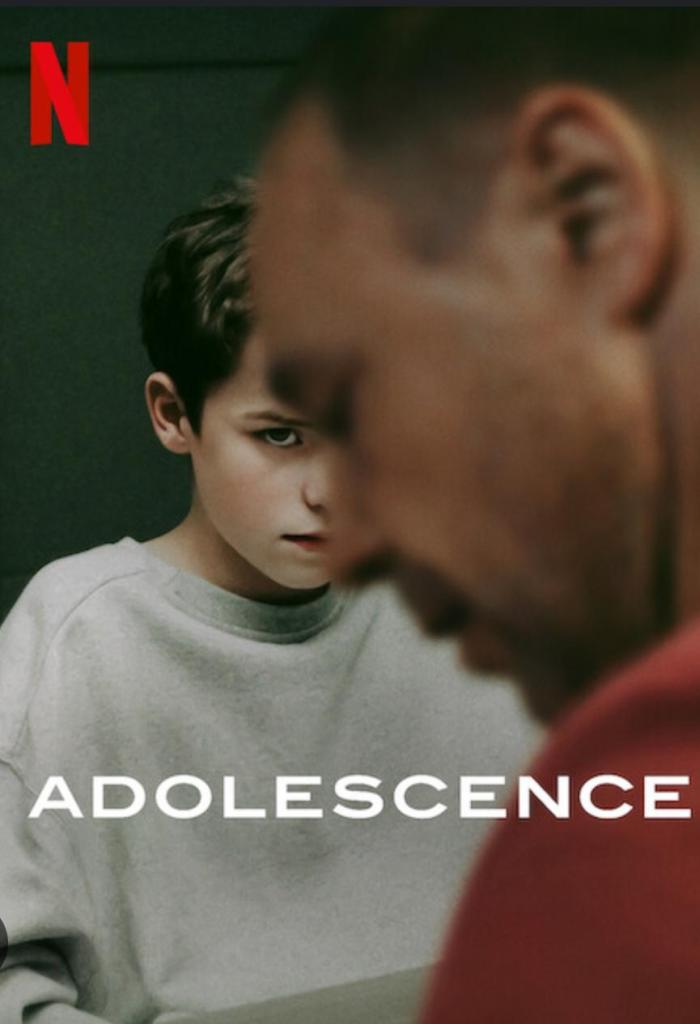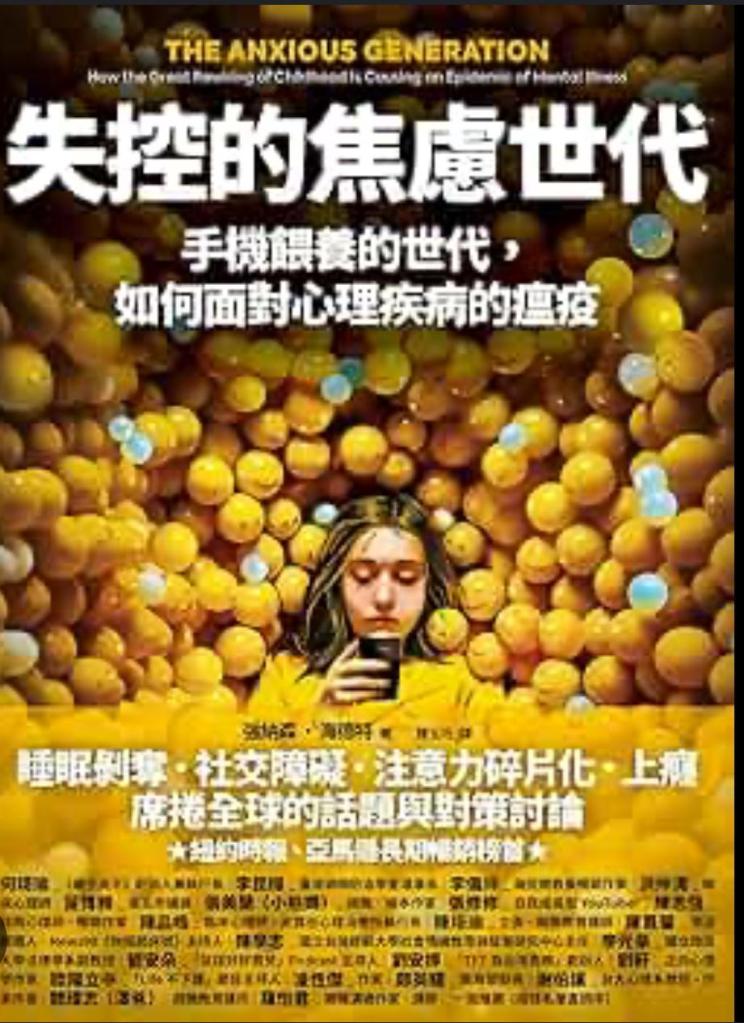◎呂慶雄
究竟香港教會的青少年流失是甚麼原因?這裡借題發揮,分享教會領䄂如何理解下一代的問題。
從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五年一次的「教會普查」報告得知,在牧者眼中,青少年流失的第一個原因是「學業壓力」(54.6%)。第二個原因是堂會「未能回應青少年需要」(47.6%),與學業壓力差不多。跟2019年的調查結果相比,排第一的都是「學業壓力」,其餘三個原因在位置與百分比上有些差異。
我猜回應者不一定是負責青少年事工的牧者,若全由他們填寫,結果可能不同。若全由仍留在教會的青少年代表回答,也許會得出更「另類」的原因。而問那些已經停止聚會的青少年為何不返教會,可能的回應是:「唔想」、「無原因」、「好悶」、「無朋友」……或者他們根本不想跟你討論。這裡只是很一般的假設,並不針對「教會普查」的方法與結果。青少年是堂會多年來不易處理的群體,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們的需要?
最近一口氣看完了Netflix的《混沌少年時》(Adolescence),同時又在閱讀海特(Jonathan Haidt)的新作《失控的焦慮世代:手機餵養的世代,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》(The Anxious Generation: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)。本來還在沉澱關於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影響的描述與分析,看到「教會普查」的報告即時反應是:若我們只從成年人及堂會的角度看青少年,可能難以對症下藥。
《混沌少年時》講述一名13歲少年Jamie因涉嫌殺害女同學Katie被捕,四集的內容提出許多引發思考的論題,如何理解成長於社交媒體下的一代成為我的焦點。其中,第二集講述負責此案的探長進入學校,嘗試透過其他學生了解Jamie與Katie的相處點滴及尋找凶器。鏡頭展示了學校的混亂、老師的不專業、學生的暴躁。探長的兒子Adam也是這間學校的學生,最後不忍父親像「盲頭烏蠅」那樣處處踫壁,於是向父親解釋如何從Jamie與Katie在IG的對話看到他們的互動。最叫人驚訝的是,青少年使用的情緒符號原來有多重意義,成人連想也沒有想過,彷彿是另一種語言。對作為警察的父親來說,需要重新理解這案的假設和發現。
第三集是Jamie與輔導員的對話,甚至可說是角力。我們看到這位少年人的不簡單。在對話中互有攻守,反映Jamie不想被成年人操控,甚至不想被了解。《混沌少年時》及海特的研究,都提醒我們不能單以大人的眼光看青少年。放回堂會流失年青人的場景,還有很多我們可能沒有想過的範疇,但因篇幅關係,這裡抛磚引玉,帶出三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話題:
在社交媒體下成長的青少年人擁有自己的語言甚至價值觀系統,沒有接觸過的成年人可以完全不明白,錯誤理解、錯誤解讀而不自知。面對成年人的不理解但又自以為明白,青少年可能的反應是:反感、抗拒、憤怒!這可會是他們不告訴你不返教會的原因?
一個行為背後可能涉及多重文化與價值觀差異。我聽過不少堂會多年來不斷努力推動青少年人的事工,卻事倍功半。同一方法,過去若不成功,未來又怎可能成功?這類堂會的領袖也許需要謙卑下來,承認自己對青少年認識不足,不適宜勉強推動青少年事工。反而可考慮與一些較有經驗的同工、事工機構多合作、交流,在堂會內外發展讓青少年覺得「自在」的文化空間。
從事工機會的角度看,影片也觸及性別議題及欺凌等校園問題,每個問題背後都不是單一原因可以解釋的。例如一般人多著眼校園欺凌的嚴重程度,卻沒有針對深層原因(執筆之際,網上正流傳香港某傳統名校的欺凌片段,發布者表示是針對校方沒有正視長期的欺凌問題!)。沒有處理深層原因,只禁止或譴責欺凌行為,於事無補。若了解到青少年面對的問題,校方或許資源不足,但教會其實尚有很多未被發掘的人才,在聆聽、同行、輔導等角色上,是否可以填補缺口,特別是那些有校園事工的教會?如此,是否更能針對性地連繫青少年的真正需要與教會事工。
前文提過海特的《失控的焦慮世代》,書中大量研究討論在社交媒體餵養大的Z世代(又被稱為zoomers、數位原生代)為何相對地更多焦慮。社交媒體鼓勵對人作出尖酸批評、排斥異類聲音以建立同溫層、把自我形象建立在流量上等等。但研究發現,帶著正面信息、鼓勵自我反思及對大自然的敬畏等的宗教活動,正正是針對焦慮世代的良藥。作者沒有說教會可做甚麼,但教會可善用已有的文化特質,針對這一代的需要來填補缺口。
回到「教會普查」報告重複揭示的問題,我最大的感觸不是數字的升降,而是當中指出的問題都不是新的,有些甚至已提出多年仍沒有改變。問題是在於難題之大無法改變?還是多年來仍找不到良方?如何理解下一代流失的問題是一個例子,告訴我們單憑自己視覺去看世界,看錯的機會是大的。成年人對青少年世界的認識,受到社交媒體的影響,距離真相愈來愈遠。探視問題的方向錯了,距離解決問題的目標便會愈走愈遠。
領導思維系列(四)